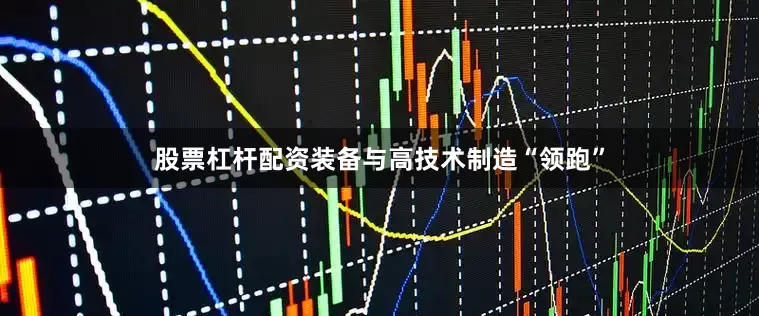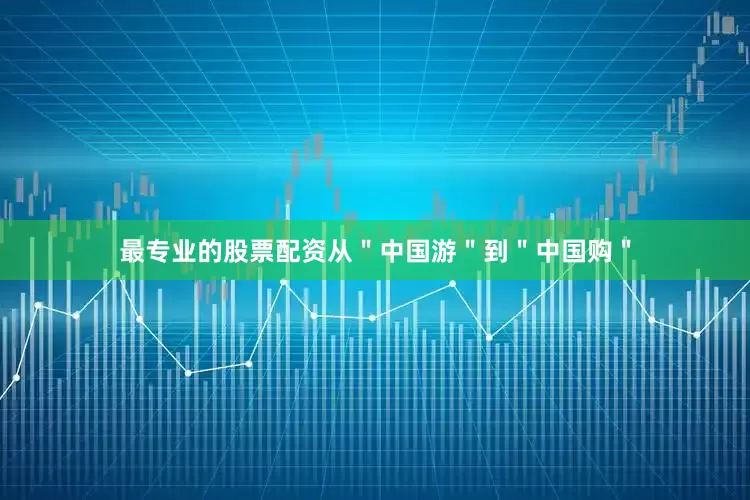曾几何时,“低空经济”四个字在我眼中如同黄金般闪耀。2023年政策东风骤起,万亿级市场规模的预测满天飞,我几乎能听到资本翅膀扇动的声音。那时,我坚信自己站在了时代的风口,手握通往未来的钥匙。
一、狂热期:被风口“吹上天”的梦想
政策狂欢点燃资本热情: “低空经济”首次写入国家规划,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发布产业蓝图,补贴政策层出不穷。每个会议、每份报告都在描绘着无人机物流、空中出租车、低空旅游的壮丽图景。
万亿泡沫的诱惑: 市场研报里动辄预测“万亿级市场”,身边投资人争抢项目份额的场面历历在目。某eVTOL(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)初创公司仅凭概念PPT就拿下数亿融资,估值飙升速度令人咋舌。
技术滤镜下的盲目乐观: 我们沉浸在“中国引领航空革命”的叙事中,选择性忽略适航认证的漫长与严苛,低估了电池技术、空中交通管理等核心瓶颈的突破难度。那些炫酷的演示视频,成了说服自己押注未来的最好理由。
二、冷静期:撞上现实的“空中楼阁”
当热情褪去,低空赛道露出了它骨感的一面:
技术瓶颈:冷酷的“适航”高墙
适航认证:漫长而昂贵的“鬼门关”:某知名eVTOL项目负责人曾私下坦言:“原计划3年拿证,现在看5年能走完流程已是万幸。” 严苛的适航标准、高昂的测试成本、模糊的审定路径,让无数技术团队夜不能寐。
电池焦虑:能量密度与安全的“不可能三角”:载人飞行器对电池要求近乎苛刻——高能量密度、极速充电、绝对安全、极端环境稳定。一位资深工程师苦笑:“航空级电池的成本,足以让商业模型瞬间崩塌。”
空管系统:技术可行≠商业可行:无人机密集区域避让算法在实验室表现完美,但面对复杂城市环境、突发天气、人为干扰时仍显脆弱。大规模运行下的可靠性与成本控制,仍是巨大问号。
商业化困境:找不到买单的“上帝”
场景之困:刚需难寻,成本高企:无人机送快递?算上硬件、运维、空域协调成本,单件配送费远超传统方式。空中出租车?百公里票价恐超千元,注定是少数人的游戏。
基建缺失:“车”造好了,“路”在哪里? 起降场(Vertiport)网络建设涉及巨额土地、审批和基建投入。某一线城市规划的试点Vertiport,仅前期论证就耗时两年,落地遥遥无期。
盈利遥遥无期: 头部物流无人机公司年营收仅数千万,却需持续投入数亿研发。某投资人直言:“财务模型显示,规模化盈利至少需10年,且前提是技术、政策一切顺利。”
政策与空域:看得见的手,打不开的门
空域开放:雷声大,雨点小:尽管政策暖风频吹,但低空空域管理权分散在军民航多个部门,协调效率低下。某通航企业CEO抱怨:“申请一条临时航线,盖章就要跑七八个部门。”
法规滞后:监管追不上创新:载人无人机的责任认定、事故处理、保险配套等法规几乎空白。监管机构态度谨慎,一位局方人士私下表示:“安全是红线,创新必须让路。”
地方主义:各自为政的“盆景”:各地产业规划同质化严重,补贴政策五花八门,导致资源分散,难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模效应。
资本退潮:潮水褪去后的裸泳者
估值倒挂:一级市场烈火烹油,二级市场冷若冰霜:某Pre-IPO轮估值百亿的低空概念公司,上市后市值惨遭腰斩,早期机构浮盈大幅缩水。
融资寒冬:故事讲完,钱袋子收紧:2024年以来,低空赛道融资案例锐减,B轮后项目融资难度陡增。FA反馈:“除非技术壁垒极高且离商业化很近,否则机构出手极其谨慎。”
退出无门:IPO收紧,并购冷淡:理想中的IPO退出通道收窄,而产业巨头对收购亏损的初创公司兴趣寥寥,投资人陷入“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”的尴尬境地。
三、转身离开:决绝背后的投资逻辑重构
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,是某明星项目的一次实地尽调。看着仓库里积灰的原型机、财务报表上触目惊心的亏损、技术团队对核心难题的闪烁其词,我瞬间清醒:低空经济不是虚假故事,但它的兑现周期远超资本耐心,估值泡沫已远超技术本身。
我意识到必须坚守投资纪律:
敬畏技术成熟曲线: 不再为实验室里的“奇迹”买单,只关注有明确工程化路径和成本控制方案的技术。
穿透商业本质: 剥去政策光环,深挖真实需求、付费意愿和可复制的盈利模式。
重视退出确定性: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确定性,优先布局技术已被验证、有清晰并购价值的细分领域(如特定工业无人机、核心零部件)。
等待真正拐点: 密切跟踪适航认证突破性进展、动力电池颠覆性创新、以及国家级空域改革实质落地信号。在此之前,现金为王。
冷静后的眺望
逃离低空赛道,并非否定其长期价值。我依然相信,当电池能量密度突破400Wh/kg、适航认证体系成熟、空域管理实现高效协同之时,低空经济终将展翅高飞。
但此刻,我选择落地。投资不是追逐风口,而是在迷雾中辨别真正的方向,在喧嚣中守护自己的判断力。 低空经济需要的不只是仰望星空的热血,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耐心。当潮水退尽,真正拥有翅膀的企业,自会飞越寒冬。
“在资本盛宴里,清醒比狂欢更需要勇气。低空经济的未来属于那些熬过技术长夜、穿越商业荆棘的实干者,而非追逐泡沫的弄潮儿。”
—— 一位曾经“狂热”的投资人
通航企业CEO关于“申请一条临时航线需跑七八个部门盖章”的抱怨,完全属实,且是当前低空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痛点。这一现象源于中国空域管理的多层级、多部门协同机制,具体分析如下:
⛔ 1. 审批涉及部门数量庞大
军方与民航双重管理:中国空域主导权属于军方(如战区空军、空域管理部门),民航部门(地区空管局、监管局)负责民用航空协调。一条临时航线的开通需同时满足军民航双方的安防、空域冲突评估等要求。
跨区域协调需求:临时航线常跨越多个管制区(如华北、华东等),需各区域空管局、地方监管局分别审批。例如华北地区的临时航线调整涉及西北、中南、东北等周边地区空管单位及中小机场,协调单位可达数十家。
地方政府及专业机构参与:还需地方发改委、交通部门(如通航飞行服务站)、空域规划设计单位、环保部门(噪声评估)等盖章。
🧩 2. 实际案例印证复杂性
华北空管局实践:大兴机场空域优化项目中,临时航线调整涉及近40个民航业内单位,包括管制单位、机场、程序设计部门等。项目采用“多项目管理模式”仍面临协调冗余问题。
通航企业反馈:行业报告指出,低空航图审批权分散在“几个关键部门”,企业需反复提交材料至军民航不同层级机构,流程耗时数月。
🚀 3. 改革尝试与遗留问题
地方简化努力:如安徽推行“皖事通办”平台,实现临时空域申请线上化,但仅适用于省内预批流程,跨省或跨战区航线仍需线下军地协同。
根本矛盾未解:军方主导空域安全的刚性要求与民航追求效率的冲突长期存在。例如,临时航线需经战区空军作战处、航管处、民航地区管理局、空管局飞行程序设计室等多环节串联审批,各部门权责独立,缺乏一站式机制。
当前低空开放进程中的真实瓶颈,反映了空域及各方面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全突破部门壁垒的现实。
尽管部分地区(如安徽)通过数字化申报提升了效率,但跨系统、跨区域的协同成本仍居高不下,成为制约通航产业发展的关键障碍。
以上不代表导向及未来。
需要强调的是,上述挑战是当前低空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障碍,而非对其长期潜力的否定。认识到这些痛点,恰恰是推动改革和优化的起点。国家层面正积极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(如湖南、江西、安徽等省份),探索“一站式”审批平台、空域分类划设等创新模式;同时,无人机运行管理(UOM)体系、城市空中交通(UAM)规则等新规也在加速构建。技术的迭代(如数字化空域管理工具)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深化,有望在未来逐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低空经济的腾飞,必然伴随着空域管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,这是一个需要政策、技术、产业协同推进的动态演进过程。
往期推荐阅读 ]article_adlist-->往期热文(点击文章标题即可直接阅读): ]article_adlist-->空军飞行员48岁改飞察打一体无人机: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--无人机飞行员李浩投身改革强军记事
挨巴铁歼10C当头五棒,急着找回场子的印度,又把以色列推进火坑
]article_adlist-->大型固定翼货运无人机鉴赏
深谋・星汉一号HW450H:450kg载重+ 820km续航!定义低空运力新标准
]article_adlist-->
]article_adlist-->
]article_adlist-->
 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,尽在新浪财经APP
海量资讯、精准解读,尽在新浪财经APP
金斧子配资-金斧子配资官网-正规实盘股票配资平台-如何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114配资网影石创新在公告中表示
- 下一篇:没有了